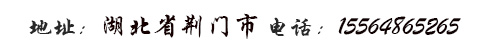花笺记曾被歌德极力称赞,欧洲人眼中的
|
中西文化的交流很早就开始了,从公元前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开始,之后“丝绸之路”逐渐形成,这条“丝绸之路”成了连接中西经济贸易的通道,为中外的交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早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年),西方文化就随着传教士的到来在中国开始传播,其中最有名的是公元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他向明神宗进献了西琴(古钢琴),并最早翻译了赞美词《西琴曲意》八章。 在文化交流时,西方人把西方文化带到我国,当然也会把我国的一些优秀作品介绍到欧洲。早在年,元杂剧《赵氏孤儿》就被翻译成法语在法国等国家流行了。伏尔泰曾将《赵氏孤儿》法语一本改编成一本五幕剧(LorphelindelaMaisondeTchao),公开演出后轰动整个法国,伏尔泰评价《赵氏孤儿》说: 其中有些合理的东西,英国名剧也比不上。 除此之外,法国人阿米奥也曾将乾隆皇帝的《盛京赋》以及其他诗歌翻译成法语,《大英百科全书》整整用了三行的篇幅介绍乾隆和他的诗。 不过,与戏剧和诗歌引起欧洲人的兴趣相反,欧洲人一直认为中国缺乏叙事性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叙事诗,黑格尔曾在他的哲学著作《美学》中说:“中国无史诗”。因为黑格尔名气太大,所以这种观点在西方有着很大的市场。实际上黑格尔根本不懂汉语,也没有来过中国,他只不过是根据早期来华西方人士的转述而形成的“中国无史诗”的印象。 对于“中国无史诗”这个观点,首先不服气的不是中国人(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黑格尔有这么一个荒谬的观点),而是一个英国人,他叫汤姆斯,是一个熟练的印刷技师,19世纪初受聘于东印度公司,为了印刷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华英字典》来到了澳门。 在澳门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汤姆斯迷上了中国文化,确切地说,是迷上了广东一带的中国文化,尤其是是对岭南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木鱼书特别感兴趣。 木鱼书又称“摸鱼歌”、“沐浴歌”,是弹词的一种,多由盲人演唱,俗称“盲佬歌”,演唱时多用三弦伴奏,从明代开始就在岭南流行。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语土音衬贴之……名日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其事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竟日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 木鱼歌行腔委婉,唱词基本为七言韵文体,四句为一组,单数句末字用仄声,双数句末字用平声,反复循环至终结。大多七言长篇的木鱼歌韵律为平韵,一节多用一韵,可以重用韵。少数木鱼歌开篇也用三字两句,有时用五字句配合三字两句用于叙写伤感的情形。 木鱼书唱腔分为妇女腔和盲公腔两类。妇女腔有点像顺口溜,一般以四个七字句为一个单元,四、三句格,随字就腔,音域在八度以内。盲公腔则行腔富于装饰性,演唱者无需化妆、布景,一人一琴即可演唱。 木鱼书最初的剧本是从佛经故事和改编的,如《目连救母》、《观音出世》等;后来有改编自小说传奇的,如《薛仁贵征东》、《白蛇雷峰塔》等;传统曲目以《花笺记》、《二荷花史》最为有名。 特别是《花笺记》,经岭南才子钟戴苍仿照金圣叹点评经典的手法对其进行评点,于康熙五十二年()以《第八才子书花笺记》为名刊行,之后名列“十大才子书”第八,在文人雅士圈子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经过差不多一百年的发展,《花笺记》在岭南文艺圈的地方更是如日中天,没有任何作品能与之抗衡。因此,这位英国印刷技师汤姆斯觉得这部《花笺记》绝对是中国最牛的作品之一,他决定将其翻译成英文,带回欧洲。 汤姆斯翻译《花笺记》,也许是为了摆脱印刷工的身份,因为著名的汉学家麦都思(Medhurst)和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都是以印刷工的身份来华,最后成了人人皆知的汉学家。也许是为了出名,做过香港第四任总督的包令(Bowring--)在年出版了他翻译的《俄国诗歌选》之后,在英国文学界引起轰动,有了极大的名气。 也许汤姆斯是真的喜欢《花笺记》,想将自己喜欢的中国文学作品介绍给欧洲。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以汤姆斯那不算熟练的汉语,只能勉强翻译一个比较口语化的说唱作品,所以,《花笺记》成了他的唯一选择。 《花笺记》作为说唱文学作品,一方面讲究节奏和韵律,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比较完整的情节,其剧本具有小说的一些特点,所以野心勃勃的汤姆斯将《花笺记》看做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企图用诗化的语言将其打造成一部“东方史诗”,以打破黑格尔的“中国无史诗”的论断,最终引起轰动,这样以来,汤姆斯这个名字不就会立即传遍欧洲? 不过,由于汤姆斯本人出身寒微,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中国文化了解不甚了解,对《花笺记》这部中文原作也不深刻,所以,他自身的文学水平不足以翻译《花笺记》,《花笺记》的英语译本于年在英国出版之后,在英语文学圈内受到无数的抨击,《评论月刊》(TheMonthlyReview)指出: (《花笺记》译本)缺少生动的叙事,尽管在形式上披着诗歌的外衣,却完全不具有诗歌的韵律,甚至很少具有超过一般水平的散文性书写。 欧洲人清醒地知道,这个锅当然不能甩给中文版《花笺记》,这完全是因为汤姆斯本身的文学水平不具备驾驭《花笺记》这样的作品造成的。 《东方先驱》曾这样评论汤姆斯译本: 汤姆斯先生似乎不懂语法,他对英语语言的美妙,也所知不多。我们相信他在很多地方都不幸地歪曲了原作。也许因为他对中国知识的一知半解,也许因为他对英语知识的了解更不全面;更有可能的是,他对两种语言都不甚了了。 尽管严苛挑剔的英国文学界大肆抨击汤姆斯这个小人物,但是对《花笺记》这部作品还是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并且也表示了对汤姆斯的某些翻译部分的认可。 《东方先驱》的评论员说: “柳荫哭别”一节,哪怕是在汤姆斯的译本中,都是极其优美的;因为心里的自然情感以真挚纯朴的方式喷涌而出。 此外,《评论月刊》与《东方先驱》的评论员都很欣赏“主婢看月”一节的翻译,前者全文引述了这节内容,认为它足以显示译作的优点;后者节录了部分译文,指出主婢间的交谈如同出自哲学家之口: Sometimehaselapsed,sinceIplantedarowofsilkenwillows, Thoughsmalltheywerethengreenandreachedtothetopofmyshoulders. Iperceiveto-day,thebrancheshavegrownlongandstout; Letmecountwithmyfingers,howmanyyearshaveelapsed. Thewesternwind,havingoflateblownforseveraldays, Iperceivetheyareblighted,andarestrippedoftheirbloominghue. Ithinkmankindingeneral,resemblethosedelicatewillows, Foronattainingmanhoodtheirautumn Whenautumnispassed,thehumantrunkbe Whohas Theblightedwillowswillagainexperiencethereturnofspring;Butman,asyet,whenoldhasneverbe 近日枝条都长大,屈指算来有几年。 近被西风吹几日,转番黄色冇乜光鲜。 我想人生亦似垂丝柳,中年就似立秋天。 秋过身衰和叶败,形容枯槁有谁怜? 绿杨尚有春归日,人老何曾转少年? 因为这段唱词没有暗喻和象征,只是以柳喻人,翻译起来相对容易,事实上,汤姆斯的这段翻译也仅仅是通顺罢了,离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中的雅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汤姆斯翻译的这部《花笺记》虽然谈不上十分成功,但是在现在看来,还是有很多价值的。 首先,汤姆斯的译本是一个中英双语的版本,上面一句是中文,下面一句是英语译文,译文虽然读起来韵律不足,但是看起来挺像诗句。而且汤姆斯译本中的中文版本与国内现存的所有版本都不一样,是一个独特的版本,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其次,汤姆斯的译本成了十九世纪欧洲人了解我国的语言文化和风俗的一个重要途径。有的读者把它当作汉语学习教材。《花笺记》的第二位英译者包令说: 汤译本附有中文原文,逐行译出(alinealrendering),对于学习汉语的人来说是一大助益。 德国著名大诗人歌德在读了《花笺记》曾对其极力称赞,《花笺记》的优美的文字和委婉曲折的情节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让他激情满怀地写下了著名的《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现枚举其中一首: 杜鹃一如夜莺, 欲把春光留住, 怎奈夏已催春离去, 用遍野的荨麻蓟草。 就连我的那株树 如今也枝繁叶茂, 我不能含情脉脉 再把美人儿偷瞩。 彩瓦、窗棂、廊柱 都已被浓荫遮住; 可无论向何处窥望, 仍见我东方乐土。 总而言之,虽然《花笺记》本身的文学成就不足代表我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上下五千年中,优秀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比《花笺记》优秀的文学作品太多了,但是,作为被介绍到欧洲去的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第一部叙事史诗,《花笺记》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anmae.com/xmsjfb/11128.html
- 上一篇文章: 草堂读诗陈先发云泥九章观银杏记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