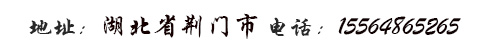猿语纳西语傈僳语,沟通起来没障碍嘛
|
从云南北边的丽江到西部的德宏,为了保护傈僳族口中的长臂猿——“甲米”,云山保护社区项目助理江婷踏上这片“长臂猿最富有诗意与人文气息的天然栖居地”。 杨江婷 云山保护社区项目助理 在那些有阳光的田野, 我能播种和收获玉米与稻谷 我是丽江人,从小说的是纳西语。丽江在云南的北边,而其余的地方是我不熟悉的——我把德宏当成西双版纳,以为西双版纳就是德宏的昵称。所以当我说要去德宏做长臂猿保护时,我妈想到的是看过的金三角电影,我爸则想象了一百种我遭遇意外的可能,我哥说我胆子真大,我朋友则推荐了无数防身器具。但我想我可是学人类学的!我什么没遇见过?你们脑内小剧场未免太多。 于是,我就来了。 来自深山的猿鸣 即使来之前,我看了一系列有关长臂猿的分布与变迁、分类与习性的文献,但是它于我,似乎依然只是等同于大学校园里的猫和松鼠,无非就是比较珍稀一些。 心态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第一次听到长臂猿叫声的那天清晨。七点的时候,我站在路边,隔着竹林与河流,积云从山顶坠落下来。天光乍泄,它就在对岸的山上啼叫。我屏住呼吸,却难耐心间激动,我多么想让我的父母、让我的朋友也听一听这猿啼,感受一下那过量的、裹挟着寒冷的氧气直往鼻孔、耳道、口腔里钻。或许我和李白听到的是同一款猿啼,但我听到的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而是来自一个确定位置的孤独猿鸣,是微弱的、懒洋洋的宛若蚊蚋。它细碎的声音一声声击打在我心里,除了激动,悲悯从我心间蔓延。我肚子叫了,不知道长臂猿有没有吃过早饭,不知道它们是歇在哪棵树上,不知道这里的天气对它们而言会不会太冷。 或许只有当每个人真正地站在那里,听到它的声音,看着往左右延伸出去无穷无尽的山脉,才会油然升起保护它们的使命感。云雾从南往北浮来,又遮盖住了山林,我舟车劳顿的身体和迷惘的内心却逐渐开始清醒、明晰。我来苏典是为保护长臂猿的,我告诉自己。 我在此岸,长臂猿就在对岸啼叫,我在寻找它,它或许就注视着我。 拍摄:杨江婷 和当地人在一起 于是我带着这样的信念进入寨子驻扎下来。每天的工作就是做访谈,问大家每个月份都去山里做什么?去哪里采野菜?蜂箱安在哪个地方?烧火都用什么木头?在哪里见到了长臂猿?收入来源又有哪些?一遍又一遍,仿佛这样我们就能得出威胁长臂猿生存的潜在因素。我雄心勃勃的长臂猿保护计划还没能持续多久就偃旗息鼓在大家自豪的“我们的祖先就会保护‘甲米’啦!去打它会出事的!(给自己招致不好的运气)”这样的语句之下。 确实,我见到的都是一群一群努力生活的乡民,是一个一个热情又朴实的人,或许那些孤独的长臂猿正是有幸生活在这里才能够拥有这片相对不受打扰的栖息地。这是我第二次心态的转变——除了动物保护,我更应该去体会当地人的生活。 或许只有沉入到人们每日劳作与情绪变化之中,我才能知道长臂猿对当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能够一起做什么。 PRA调查中,梨树寨子的曹社长在绘制社区资源图 拍摄:杨江婷 当我们翻过山坡,避开荨麻,体验了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竹笋的采集过程;当我们在烈日底下晒谷子,每天下午两点准时去喂猪草,结束了访谈顺路去地里摘一些黄瓜和玉米回家的时候;也当大家在朋友圈发着小视频感叹打笋子的辛苦,却还拿着卖竹笋得来的钱大方地请我们吃烧烤喝饮料的时候。 我深切地体会到,我们做的动物保护,是充满着人文关怀的,并且还收到了来自大家的反向关怀。大家在地里撒下秧苗,种下玉米,为了收成开心,为了生活烦恼,又潇潇洒洒对酒当歌。我跟着大家大笑,也跟着大家叹气,再吃下一碗米酒晕晕乎乎不管明天。 一碗米酒下肚则晕乎乎 拍摄:杨江婷 余金大哥亲自下厨请我们吃石板烤牛肉 拍摄:杨江婷 哄小朋友说我给她画个花戒指 拍摄:杨江婷 小朋友摘回来的野果,酸到只能当插花了 拍摄:杨江婷 滑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anmae.com/xmxwgj/11132.html
- 上一篇文章: 过敏体质自测9种最该警惕的过敏原就在你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